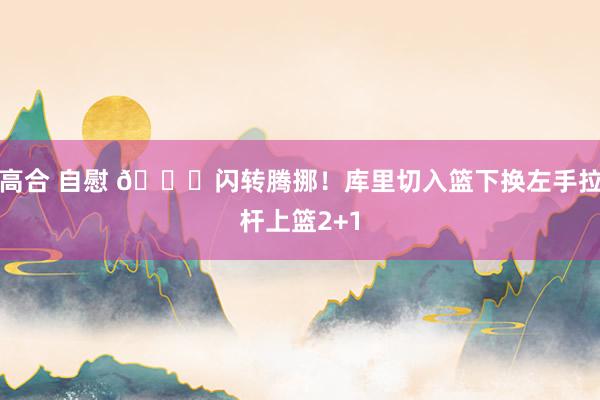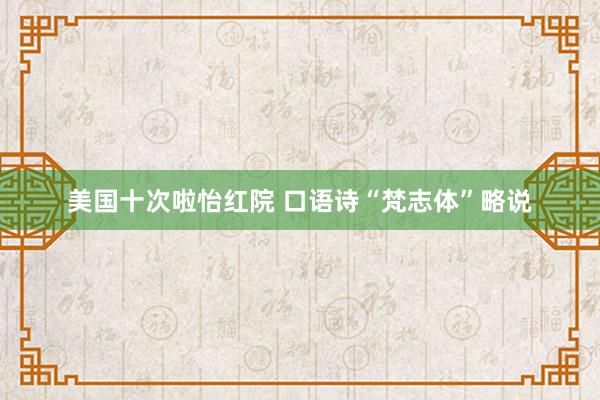
梵志体因文东说念主学习王梵志口语诗而得名,但历来记录言之省略美国十次啦怡红院,兹梳理如次。
传世文件最早言及该诗体的是李壁开禧三年(1207年)至嘉定二年(1209年)谪居抚州时撰出的《王荆文公诗李壁注》,卷四三注《示李时叔二首》其二“千山访我几摧辀”时说:“刘琨诗‘骇驷摧双辀’,王维‘梵志体’诗云‘何津不饱读棹,何路不摧辀’。”刘句出《重赠卢谌》,王句出《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东说念主二首》其二,因此,注中“梵志体”当指王维的两首诗。嗣后,宋末元初刘辰翁《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》卷三《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东说念主》题下有注云“二首梵志体”,明顾起经注《类笺唐王右丞诗集》卷一在诗题下又说“刘校,本注云梵志体”,过往学东说念主对此颇多争议,或以为“梵志体”不是王维自注,而是刘辰翁评点王诗时的批语。从李壁注看来,“梵志体”应是王诗原题自注,李壁致使用它替代王的诗题。此外,唐雯《晏殊〈类要〉计议》从《类要》卷三〇《咎征》发现了一条有劲的干证——卢照邻佚诗《营新龛窟室戏学王梵志》,既然前辈著明诗东说念主都戏仿过王梵志诗,那么,后辈王维作梵志体也不错清醒。不外,与此前诗坛鉴戒前世或当世名家(如《南都书》卷三五说萧曅“诗学谢灵运体”、《周书》卷一三说宇文招“学庾信体”)不一样的是,卢、王学习的是民间口语诗。
敦煌保存的王梵志诗,主要有三卷本、一卷本、法忍手本、零星手本和引证诗(如《历代法宝记》引“惠眼近空腹”等四句)。但吊诡的是,传世文件援用的梵志体基本上莫得与敦煌本都备疏通者。这就促使咱们念念考如下问题,两类文件中的王梵志诗是否具疏通属性?
唐五代传世文件中蹙迫的有:皎然《诗式》卷一“放诞格二品”,它最初把王梵志《说念情诗》与郭璞《游仙诗十九首》之六、贺知章《放达诗》、卢照邻《漫作》(皎然仅引两句,《类要》卷三〇引有“城狐尾独束”等五句,亦然《漫作》佚句。换言之,卢氏至少有两首梵志体)等量都不雅而归入“骇俗”品,谓诸诗特质是“外示惊俗之貌,内藏达东说念主之度”。宗密《禅源诸诠集都序》,则把王梵志、志公、傅大士当作“降其迹而适性,一时分警策群迷”的弘法代表。范摅《云溪友议》卷下《蜀僧喻》又载,玄朗上东说念主“或有愚士昧学之流,欲其开悟,别吟以王梵志诗”,并评王诗“其言虽鄙,其理归真”。敦煌本《王梵志诗集序》谓王梵志“制诗三百余首,具言局面,不浪虚谈……不守经典美国十次啦怡红院,皆陈俗话。非但智士回意,实亦愚夫改容。遐迩传闻,劝惩令善……纵使大德讲说,不足读此善文”,对读两类文件之后,不难发现它们都强调王梵志诗特质是:内容迫临社会生存,话语俚俗,功在劝化,后者致使觉得读梵志诗远比听释教讲经更有好事果报。
卢照邻《营新龛窟室戏学王梵志》“试宿泉台里,佯学死东说念主眠。磷火寒无焰,泥东说念主唤不前。浪取蒲为马,花费纸作钱”,是现有最早的文东说念主梵志体,若与其传世的同写佛龛题材及存一火主题的《相乐夫东说念主檀龛赞》“猗欤宝相,显允神功。鸿沟鹿苑,图写龙宫……一窥妙境,高谢尘蒙”比拟,一诙谐,一悠闲,格调迥异。而前者所写“纸钱”的丧葬习惯,敦煌本王梵志诗亦然,如“积贮留妻儿,只得纸钱送”“一日阙摩师,空得纸钱送”等。
玉足吧据项楚先生《王梵志诗校注》统计,今存王梵志诗约390首,366首出自敦煌遗书(其他24首散见于历代条记、禅宗语录等)。它们都很是宠爱平常生存书写,挑剔最多的话题除了生、死之大事外,“钱”字的使用频率也很高,致使杰出“佛”和“菩萨”(初步统计,敦煌本“钱”字出现34次,“佛”“菩萨”各为23次、2次),此讲明民间诗东说念主更关注经济生存而非宗教精神生存(如王维387首、李白近千首诗中仅别离有2次、7次言及财产道理的“钱”字,频率远低于王梵志)。传世文件言及“钱”字的梵志诗还有《云溪友议》卷下所引“欺枉得钱君莫羡,得了却是输他便”“都头送到墓门回,分你财帛各头散”“多置庄田广修宅……哭东说念主满是分钱东说念主”等三首,以及行秀《请益录》卷下引晋阳贾文振所诵王梵志“我若有钱时”“我若无钱时”二诗,行秀谓它们“激讽诸东说念主,不为不切矣”,这讲明经济要素在宗教生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如斯风风火火地谈“钱”,在正宗文东说念主诗歌中少量见。
传世文件中流播最广的王梵志诗有三首:一是《诗式》所引《说念情诗》,二是黄庭坚所书《梵志翻着袜》,三是惠洪《冷斋夜话》卷十所引《城外土馒头》。三东说念主中,两位是诗僧,黄是居士,都很是老到佛典与释教文化。黄庭坚还止境点明“梵志是大修行东说念主也”,行秀《沉稳庵录》卷五亦称“王梵志奇东说念主,此语大播东说念主间”。南宋以降,用“翻着袜”上堂说法者不堪摆列,原因在于它体现了禅者反常合说念下的自适其性,它与“骇俗”所说“达东说念主之度”的“达东说念主”实质是疏通的。据《大慧普觉禅师语录》卷三载,北宋大不雅年间(1107—1110年)的侍郎魏矼“常以王梵志《土馒头颂》作佛事,以警觉流俗”,则知该诗与敦煌本其他王诗的功用如出一辙,皆在警醒众东说念主。不外,苏轼、黄庭坚、释克勤、刘克庄、牟巘、刘辰翁、方回、释净范等僧、俗二众用申雪法对“土馒头”,惠洪、陆游、赵秉文、姜特立、钱谦益、孙枝蔚、陶元藻等对“翻着袜”语典之诈欺,都有创造性的发展,写出了不少有另类幽默感的诗偈,如王如锡辑《东坡养生集》卷七“达不雅”条就觉得苏轼把王梵志“土馒头”诗后两句改为“事前着酒浇,图教隽永说念”,是“改得有理,亦有致”。
两宋以降的两类作品,可纳入梵志体:一是像卢照邻、王维那样径直在落款中就揭示诗体性质者,如陶望龄《袁伯修见寄效梵志诗八章拟作》、陶奭龄《袁石浦先生作梵志诗见寄效作七章》、董暹《读梵志诗四首》、王宗燿《戏易王梵志诗三首》等。诸诗皆话语浅俗,富于禅趣:如陶望龄第六首“泥馒头里肉馅,四板汤中糁头。好趁庖东说念主未到,权时抹粉搽油”,一样由“土馒头”生发想象,但用四板汤指代棺材,更切合南边的土葬场景,末后两句则标明晚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社会风俗;陶奭龄第七首“蓼虫苦中作活,蜜蜂甜里餬口。苦则终生自受,甜应总为他东说念主”,以天真道理的譬如、对比来揭示基层环球餬口之不易;董暹第二首“我手怎样佛手,我脚怎样驴脚。夜来欹枕熟眠,驴佛一时抛却”,用梦来解构禅宗公案“黄龙三关”(生缘、佛手、驴脚),委托了东说念主生如梦、起因性空的念念想;王宗燿第三首“城外土馒头,馅草在城里。可惜林檎树,儿生已无味”,其申雪法用到极致,尽然把听说出生在林檎树瘿中、自后始创翻着袜的王梵志本东说念主也当成馅草,这标明任何东说念主都逃不出物化是生命当然经过的轨则。二是化用王梵志诗意或诗句者,如秦不雅《和裴仲谟〈摘白须行〉》“是以梵志云:昔东说念主已非昔”,就隐括了“吾家昔浪费,你身穷欲死。你今初有钱,与吾昔相似。吾今乍无初,还同曩昔你”的旨意;楼钥《走笔送僧义冲》“梵志有至言:还我未生时”、《戏题珪老借庵》其二“不知当初问谁借,于今久假而不归。毕竟还了方是了,却须还我未生时”,王若虚《再致故居述怀五绝》其五“艰危尝尽鬓成丝,转觉高贵不行期。几度哀歌仰天问,怎样还我未生时”等,皆从《说念情诗》化出,充满了对生命个体终极道理的追问,袁枚《随园诗话·补遗》卷十第九条论“诗有见说念之言”即说王梵志此“八句是禅家上乘”,因为“未生时”与南宗禅“无位真东说念主”的念念想内涵确有重复之处。
综上所论,自初唐至晚清,文东说念主梵志体诗虽未成鸿沟,但它们多在释教居士手中彼此传习,独具特色,故也具有较高的诗歌史价值。
(作家:李小荣美国十次啦怡红院,系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计议中心教学)